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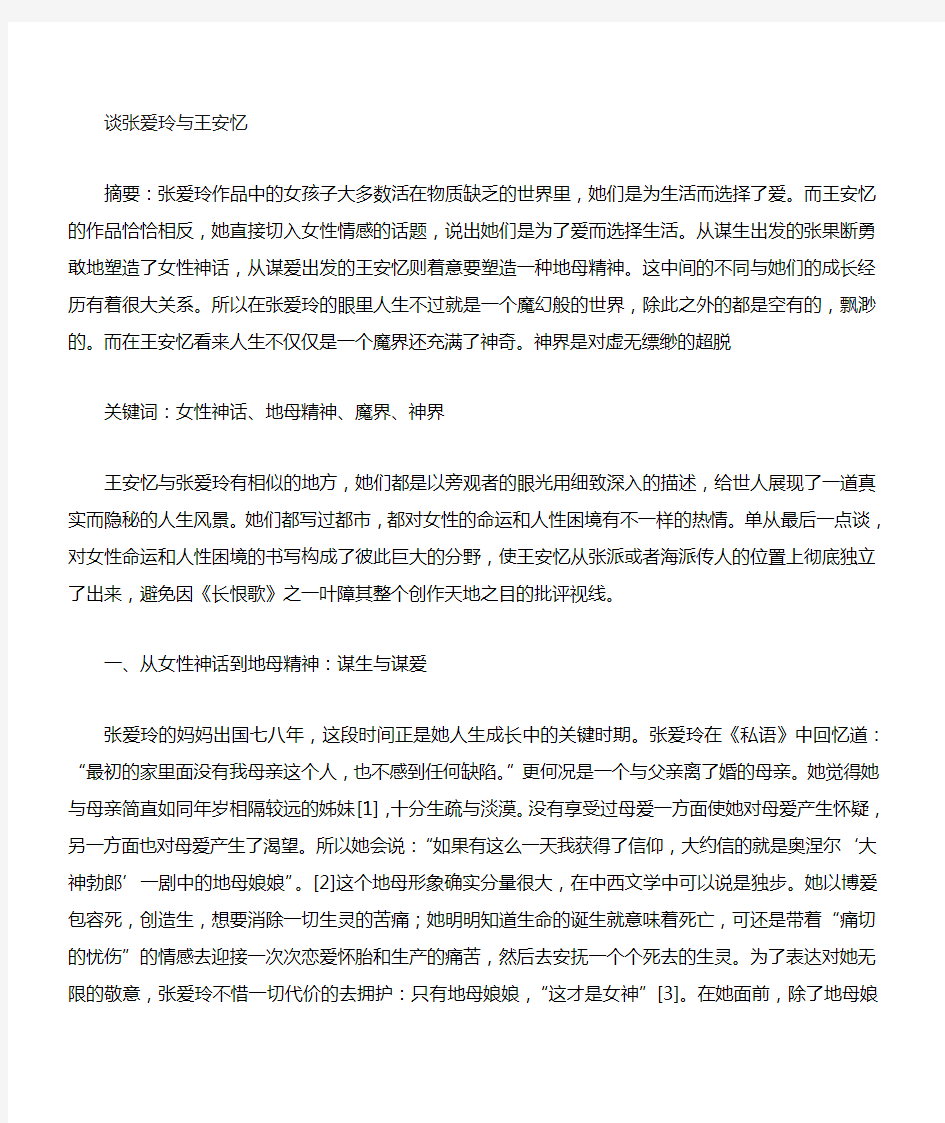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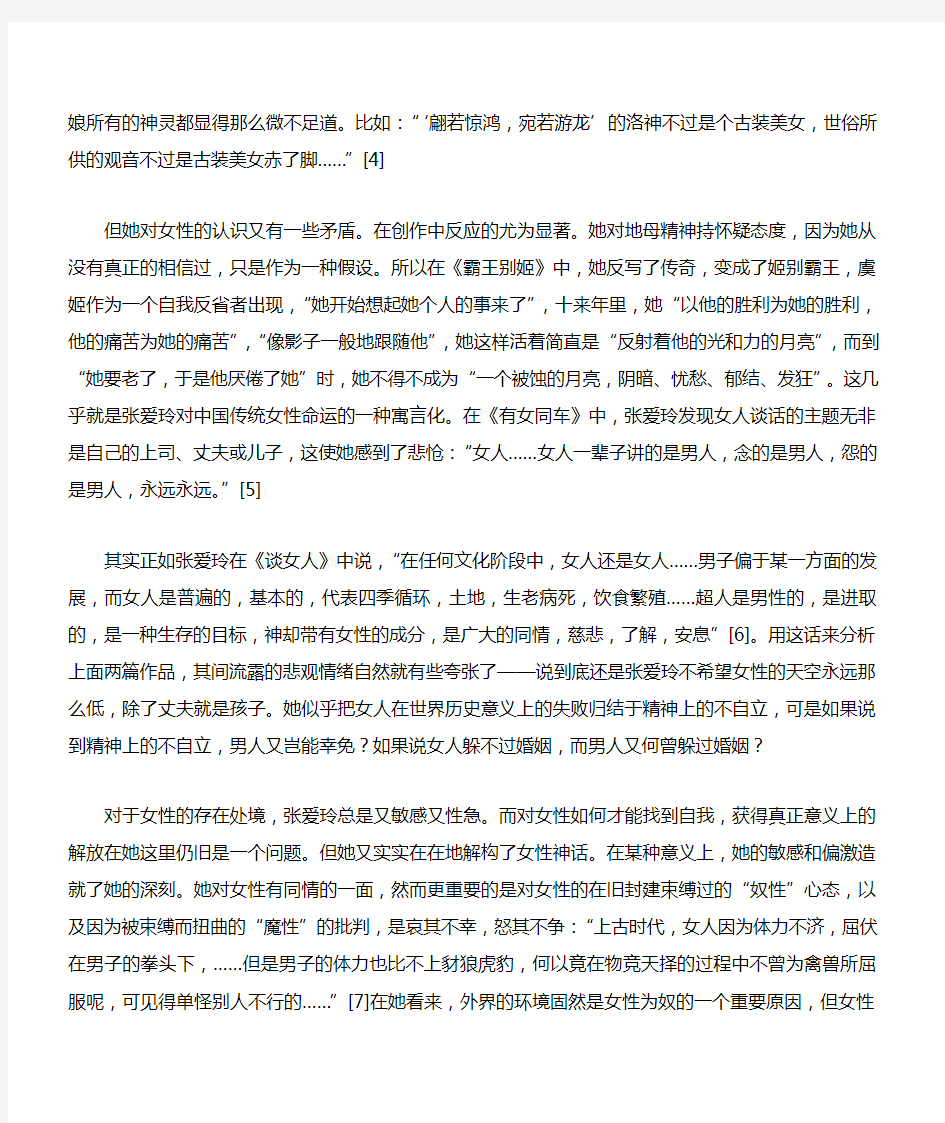
谈张爱玲与王安忆
摘要:张爱玲作品中的女孩子大多数活在物质缺乏的世界里,她们是为生活而选择了爱。而王安忆的作品恰恰相反,她直接切入女性情感的话题,说出她们是为了爱而选择生活。从谋生出发的张果断勇敢地塑造了女性神话,从谋爱出发的王安忆则着意要塑造一种地母精神。这中间的不同与她们的成长经历有着很大关系。所以在张爱玲的眼里人生不过就是一个魔幻般的世界,除此之外的都是空有的,飘渺的。而在王安忆看来人生不仅仅是一个魔界还充满了神奇。神界是对虚无缥缈的超脱
关键词:女性神话、地母精神、魔界、神界
王安忆与张爱玲有相似的地方,她们都是以旁观者的眼光用细致深入的描述,给世人展现了一道真实而隐秘的人生风景。她们都写过都市,都对女性的命运和人性困境有不一样的热情。单从最后一点谈,对女性命运和人性困境的书写构成了彼此巨大的分野,使王安忆从张派或者海派传人的位置上彻底独立了出来,避免因《长恨歌》之一叶障其整个创作天地之目的批评视线。
一、从女性神话到地母精神:谋生与谋爱
张爱玲的妈妈出国七八年,这段时间正是她人生成长中的关键时期。张爱玲在《私语》中回忆道:“最初的家里面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更何况是一个与父亲离了婚的母亲。她觉得她与母亲简直如同年岁相隔较远的姊妹[1],十分生疏与淡漠。没有享受过母爱一方面使她对母
爱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也对母爱产生了渴望。所以她会说:“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神勃郎’一剧中的地母娘娘”。[2]这个地母形象确实分量很大,在中西文学中可以说是独步。她以博爱包容死,创造生,想要消除一切生灵的苦痛;她明明知道生命的诞生就意味着死亡,可还是带着“痛切的忧伤”的情感去迎接一次次恋爱怀胎和生产的痛苦,然后去安抚一个个死去的生灵。为了表达对她无限的敬意,张爱玲不惜一切代价的去拥护:只有地母娘娘,“这才是女神”[3]。在她面前,除了地母娘娘所有的神灵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比如:“‘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4]
但她对女性的认识又有一些矛盾。在创作中反应的尤为显著。她对地母精神持怀疑态度,因为她从没有真正的相信过,只是作为一种假设。所以在《霸王别姬》中,她反写了传奇,变成了姬别霸王,虞姬作为一个自我反省者出现,“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十来年里,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像影子一般地跟随他”,她这样活着简直是“反射着他的光和力的月亮”,而到“她要老了,于是他厌倦了她”时,她不得不成为“一个被蚀的月亮,阴暗、忧愁、郁结、发狂”。这几乎就是张爱玲对中国传统女性命运的一种寓言化。在《有女同车》中,张爱玲发现女人谈话的主题无非是自己的上司、丈夫或儿子,这使她感到了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5]
其实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说,“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超人是男性的,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6]。用这话来分析上面两篇作品,其间流露的悲观情绪自然就有些夸张了——说到底还是张爱玲不希望女性的天空永远那么低,除了丈夫就是孩子。她似乎把女人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失败归结于精神上的不自立,可是如果说到精神上的不自立,男人又岂能幸免?如果说女人躲不过婚姻,而男人又何曾躲过婚姻?
对于女性的存在处境,张爱玲总是又敏感又性急。而对女性如何才能找到自我,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在她这里仍旧是一个问题。但她又实实在在地解构了女性神话。在某种意义上,她的敏感和偏激造就了她的深刻。她对女性有同情的一面,然而更重要的是对女性的在旧封建束缚过的“奴性”心态,以及因为被束缚而扭曲的“魔性”的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伏在男子的拳头下,……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竟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不行的……”[7]在她看来,外界的环境固然是女性为奴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女性生生世世做男人牛马,甚至力争去做牛马则是女性自甘为奴的根本原因,也是女性个性解放的最大障碍。
所以张爱玲只能以解构女性神话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女性解放的理解,尽管她十分崇尚地母娘娘,但她的作品总是只有一点“地母的根芽”[8],到了曹七巧这个最彻底的人物,连这一点都泯灭了。
而王安忆在创作之初就仿佛于冥冥之中从张爱玲那里接过了“地母的根芽”,而且把它越做越大,创造了许多近乎地母的形象,并解析出一套明确的“地母的精神”。她似乎是凭着一种女人的本能,达到了极高的领悟能力。
《流逝》中的欧阳端丽,是王安忆最初塑造的一个饱满丰厚的女性形象。在家庭不幸面前,丈夫拿不出男人气概,欧阳端丽这个昔日的千金小姐一改对丈夫的依赖,显示出主妇的魄力。她辞掉阿姨,包下所有家务,精打细算过日子……却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爱家庭,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她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保护人,很骄傲,很幸福。”
这似乎是在重塑一种女性神话。对于女性神话,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指出:“没有比女性神话对统治者更有利的神话了,它确立了所有的特权,甚至使男人的诅咒也显得权威起来。”[9]但其实不是。王安忆是塑造了一种地母精神。这与王安忆对女性解放的深刻思考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思考不是单独面向女性,而是涉及到男性,“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那么一个问题:究竟,男人是怎么回事,女人又是怎么回事?”[10]
“寻找男子汉”,一度喊出了20世纪80年代女性的心声。而王安忆却认为,这“或许是女人永恒的困惑与失望”[11]。因为她认识到:“在中国,男人的机会很少,他们也很难去发展。又要他们发展得好,又要他们适应各种情况,要温和,又不失男子气概,还要满足女性的各种要求,那该多难!”[12]
王安忆的这种认识显现出眼光的犀利来:中国的女性解放已经搞了这么多年,可女人们总算是放开了自己,开始了大胆寻找生命真爱的历程,可寻来寻去,还是在旧的思维模式里,认为“男人应有宽阔的胸怀和肩膀,可容下一世界的苦难并承起一世界的重任”。而为什么一定要寻找男子汉?这本身就是女人的误区。终究还是女性潜意识里仍旧把自己当做弱者,希望自己能够依附于男人的传统心理在作祟。所以她说,“寻找男子汉,也许注定不会有结果。男子汉或许都在陪伴不致力于寻找的,要寻找的永远寻找不到。”[13]
在《女作家的自我》中,王安忆更直接地质问:“做女人难,做男人还难不难呢?”[14]在《长恨歌》中,她描写李主任的一段话体现了她对男人的深刻同情:“李主任这样的风云生涯,外人只知李主任身居高位,却不知高处不胜寒。各种矛盾的焦点都在他身上,层层叠叠。最外一层有国与国间;里一层是党与党间;再一层派系与派系;芯子里,还有个人与个人的。……李主任是在舞台上做人,是政治的舞台,反复无常,明的暗的,台
上的台下的都要防。”
“我觉得这个世界是男人的社会,男人的世界真的是很大很大。一个男人不能全部爱你的话,他是有很多理由的。”[15]王安忆这话一方面是对男人的理解,一方面也是对男权社会的无奈认同。因为,“男人的理想是对外部世界的创造与责任,而女人的理想则是对内部天地的塑造与完善。”[1 6]王安忆从女人对于大历史的隐退中,探求女人的存在。对于男女不平等,她把部分原因归结为自然弄物所造就的性别差异上。“自然的安排总是那样强差人意……人注定生活在缺憾中,人与自然永远在较量,以求获得完满的平衡而永远也获不到。写到此,不禁觉得生命是一桩很累的负荷物,性别也是一桩很累的负荷物。可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庆幸生存,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暗暗庆幸自己性别的所属,为这性别迎接并争取着非它莫属的欢乐。这就是自然,无论有多少不合理,也唯有承认了。”[17]她的思考总算有了结果,尽管是无奈的诠释,却也追寻到一个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很务实。这与作家的生活态度有关,“我对生活采取了认可的态度,生活应该是这样的,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心平气和,承认现实,直面现实,就行了,就胜利了,所以我的胜利不在于我成为一个作家,而在于我的心境平静下来。婚姻是具体的,但生活中有许多乐趣,承认它,面对它,平静下来,就战胜了自己。”[18]“对我来说,一个女人怎样去塑造自己是很重要的。”[19]她首先分析了男性心理,而得出了“自我塑造”的结论。所谓女性的“自我塑造”,在她看来,决不是贸然向男性社会宣战,因为女性的失败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有其历
史必然性,所以女性需要在认同既定模式即十分务实的前提之下,做力所能及的绵里藏针的争取,也就是凭借女性自身的优势和实力在男权社会中坚定地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女性解放的策略。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是王安忆对张爱玲《倾城之恋》中“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意境的改写。在《倾城之恋》中,香港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苏与范柳原本来十分缥缈的姻缘,“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流弹没能够炸死他们,却将他们的相互算计都毁灭了,只剩下简单的一对劫后余生的男女,相濡以沫的,结了婚。如果说《倾城之恋》是作家意欲通过男女主人公最后的相知相许,表达一种由于战火中个人生死未卜而冉冉升起的一股对于爱情和亲情的的神往;那么《死生契阔,与子相悦》则是在着力以工笔描写女性对于家庭不幸的毫不畏缩的承担,体现了作家对于女性认识的不同境界。前者的女性因为城倾而从男人那里获得了真实的爱情和婚姻的保障,后者的女性却是因为城倾(如果说“文革”也导致了一番不同意义上的翻天覆地),而给予男人真实的爱情和婚姻的保障。这些男人在不幸来临时闯祸的闯祸,躲的躲,病的病,他们的女人却处变不惊,放下身段,持家度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女人也依旧高贵美丽,不失优雅。她们能在红卫兵的监视下淘米,不疾不徐地回答他们的质问。她们也能在买菜的路上,打一缸淡豆浆回家慢慢享用。而这不分明是
一派与子相悦,死生契阔(——既然已经与你相爱了,生死又怎能不置之度外呢)的境界?也由不得作家要感叹:“这些女人,既可与你同享福,又可与你共患难。祸福同享,甘苦同当,矢志不渝。”[20]。
对于婚姻,张爱玲早在圣玛利亚女校读书时,就把有天才的女孩结婚视为天底下最大的恨事。而且,她的确和许多作家一样是把婚姻和家庭当做人类一大困境来书写的。王安忆不然。她借评论王昭君提出自己明确的看法:“王昭君不嫁人,倒是清静美人,最终不就还是个白头宫女。出了嫁,自然就有姑舅,那就要处理和解决,缠进家务事中。用不着雄心大略,可却是世故人情,有着做人的志趣和温暖的。大美人盘旋在俚俗琐事中间,真有点‘地母’的形容呢!”一个个女人“麻缠在俗事俗务中间,却透出勃勃然的生气。她们的精力一律格外的充沛,而且很奋勇,一点不惧怕人生,一古脑地投进去”[21]。
作为女作家,王安忆对女性生存现状和价值取向有着近乎本能的关注和理解。她站在女性自身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并开始在女性自身寻找问题的症结,甚至试图为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帮助。妇女解放的问题是通过王安忆笔下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来阐释的:欧阳端丽、逢佳、王琦瑶、妹头、富萍……她们是王安忆理想中的女性,为了自己的目的,不论是爱情还是婚姻,虽九死而不悔,“我比较喜欢那样一种女性,一直往前走,不回头的,不妥协,但每个人,每个人物都有它的局限性,一直往前走,也可能最终把
她自己都要撕碎了,就像飞蛾扑火一样。”[22]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生活在物质匮乏的恐惧中,是为谋生而谋爱。以《连环套》中的霓喜为烈。而王安忆使自己超越于张爱玲的地方,或许也在于她通常在张爱玲止步的地方直接切入女性的情感世界,是为谋爱而谋生。她根本不让自己笔下的女人有物质的匮乏感,而重在探讨她们的情感需要。《香港的情和爱》中逢佳虽然起初是处于经济的考虑依附老魏,但很快彼此就萌生了真感情。而最终彼此的分离,也是处于感情的考虑。这显然是不一样的境界。
从谋生出发的张爱玲非常果敢地解构了女性神话,潜在提出女人应当为自己而生存的命题;从谋爱出发的王安忆则是着意要建立一种包容一切的地母精神。这种不同与她们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因此张爱玲看到的人生是一个魔界,魔界之外就是虚无。而王安忆看到的人生之中还有一个神界隐约在魔界之上。
二、人性在困境中沉沦或升华:魔界与神界
张爱玲和王安忆都是善于写人情练达小说的优秀作家。她们都会不遗余力地将笔墨耗费在人物的日常起居、待人接物及其伴生的心计上。然而,究其根源,二者的旨趣大相径庭。
幼年经历的不同,使得两作家对世界的感知从一开始就迥异,导致彼此成年后的写作视点截然不同。张爱玲家庭的不幸使她的感悟中有非常人所可以道的切肤之痛。而王安忆在一种安静祥和的家庭气氛中成长,她的感悟则更带有一种普遍性经验,如《69届初中生》虽说是以雯雯为主人公,讲的却是一代人的故事,而王安忆对《长恨歌》的写作理想是要通过一个女人讲一个城市的故事一样,而张爱玲却只是打算讲述几个上海的传奇或是香港的传奇,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对城市、时代的叙事冲动。在王安忆层层铺垫的日常生活背后透着的是人面对自己面对时间的虚无,在张爱玲悲剧主人公身上所散发的虚无气息之外是他们对于日常生活的无奈而绝望的执着。王安忆关注的是虚无后的奋进,即无望地抗战虚无——这种虚无不会因为人物的反抗而有所淡化,而令人如陷沼泽;她总是希望在并不安稳的人生中寻求一些“飞扬”的东西,尽管结果总是不尽如人意,她还是完成了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寻求。张爱玲关注的是虚无后的绝望和无奈,是对虚无状况的彻底认同,可以毫不夸张地将她定位为一个虚无主义者。因此,张爱玲在虚无之后更注重人生安稳即现实的一面,她因为近乎绝望地向往现世安稳,而忽略和否定了人生飞扬的可能性。
人总是会陷于种种困境,或者说苦难,作为一种存在本身,它的确是
会过去和消失的;但作为一种普遍的存在,它就将贯彻在人类的整个生存之中。因此,困境是人存在的基本状况,或者说,人就是害怕苦难而又不能不忍受苦难的一种存在。而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个在困境中体验到痛苦同时也快乐着的文学形象,即加缪笔下的西西弗。加谬通过西西弗这个形象阐释了这样一种观点:生活如果确实荒诞无意义,那么就更应该好好地去经历它。他认为:荒谬是维系人与世界关系的唯一纽带。如果人意识到荒谬就不再生活,那就取消了意识的反抗。消除荒谬,是一种反抗,以火一样的激情去穷尽一切,就能领悟到生命的价值。以西西弗来比较王安忆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我们便会发现,她们二者从人的存在的拷问上来说是有差别的。在张爱玲笔下,人被环境困住便身不由己地不断下陷。在王安忆笔下,人不甘于被困境束缚而力求突围。
从王安忆的散文《情感的生命》可以发现,她曾仔细阅读和研究过加谬的作品。难怪她笔下的很多人物都有一股西西弗的意味。对于《我爱比尔》的阿三,如果排除道德焦虑的干扰,阿三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西西弗。她的想法很荒谬,但她从不放弃这个想法,坚持付诸行动。小说中,她对美术评论家说她作画是“因为快乐,这同几年前的说法一致,语气却要肯定,经过深思熟虑的。”评论家很奇怪:说是为了快乐,画面却透露出痛苦。阿三却说出了“快乐和痛苦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濒临绝境的情感”这样富于存在主义哲学意味的话。在这一层意义上,阿三和西西弗一样,都是荒谬的英雄。在王安忆的小说中,有很多这样的身影,她们可以是张达玲、项五一、妙妙……但白流苏们就不一样了,她们对于自己的人生也有抗争,也
有挣扎,但多在一种物质的或者说简单的情感层面上,所以她们对困境只是想着如何逃避和摆脱,对自己身上的人的存在也没有任何发现,她们只是被动、无奈地活着;她们不是生活的主人,而只是被生活裹挟着往前走的人。无论是白流苏,还是葛薇龙,她们都是被困境所捆住的人,没有任何能力承担命运,也没有任何一刻有“痛苦的清醒意识”。她们所有的力的展现,所有的富于心计的争取的只是衣食的无忧、短暂的情爱。
从外在看,阿三、王琦瑶对于人生更多一些精神上的把握和追求,不是简单地为物所困,为情所困。而从内在看,她们有自己的主体性,尽管这种主体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畸形的。所以,她们二人对于人类困境的揭示各有侧重,只能见仁见智。充沛于张爱玲小说的各式各样又大同小异的旧式家庭人事纠葛,其实就是同一主题的复奏,通过对困境的细致描摹,把人物的悲惨命运尖锐地揭示出来;中国几千年来的人情世故的困境在她笔下得到优雅而残酷的展现。她笔下的人物一出现,就几乎是开始了走向没有光的所在的历程,她根本不想或者也没有想过要赋予她们一种精神上的攀高。
张爱玲写的是人在芸芸众生中的沉沦,而王安忆是要写人在芸芸众生中的升华,是凡俗中的英雄心,神性的光芒。“我以为,艺术与真实区别其实就在于此……沉沦平庸也终是人类的不幸……这种东西,我们命名为英雄,他们与古典的英雄不同,他们不是神诋下凡,是脱生于芸芸众生,是凡世的升华。”[23]
比如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张爱玲只给她一个季泽来做爱情的幻想。当这唯一的幻想因为季泽奔她的钱而来终于破灭后,她泯灭了自己最后的人性,彻底成为物质的牺牲品,进而一个本来是不幸命运的承担者的可怜女人,摇身一变成为自己亲人不幸命运的制造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是在不幸中被扭曲变形,最终把自己堕落为十恶不赦的魔鬼的过程。这就非常现实也非常深刻。
而王安忆正好相反。她不是这么现实。她也是对现实有深刻认识的作家,但她并不想把现实推向绝境,让人物变态,成为环境的牺牲品或是恶的化身。她总是想尽可能多给人物制造出一些合乎情理的机会,让她们在现实的困境里多战斗几个回合,即使失败,也距离神界更近一点。好比西西弗推石头,虽然结果很可能是一样的,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意识更为浓烈,这是一种近乎中国儒家入世态度的人生选择。
对于人情世故阴暗面的表达,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已经达到极致。她笔下的人物视野范围很窄,都被挖掘得很透彻,人物几乎被透明化。这些缺乏外界新鲜气息影响的没落男女形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天地。在她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敞开的魔界。而王安忆却有点类似于堂吉诃德的味道,似乎要让人物揪着自己的头发,向神界出发。所以她善于描摹诩诩如生的新市民,这些人物充满了向上的渴望和力量,对现实决不服输,而且在和现实的争取和搏击中获得了对人生及其不幸的感悟和超脱。对张爱玲而言,人生的虚无是因为人生就是一个魔界,充满了无意义的喧嚣和骚动;而对于王安忆,人
生的虚无并不是空,因为在人生的魔界上面,还有一个神界,在它的照耀下,人生的点点滴滴都是意义与生命的诠释。所以,同样是表现人生的困境,日常生活中人性的自私和冷酷无情,二人的笔致有很大不同。也许,张爱玲的身世有一点寒气逼人,她总是冷眼看世界,这种“冷”促使她把人生看得很阴冷。王安忆则不同,她始终有一股热血意识在那里撑着,所以她的都市书写张扬、铺陈,在繁复细腻间中改写出与张爱玲截然不同的一番天地。她们两人对于人情世故都看得非常透彻,但张爱玲看着看着就有些看破红尘的味道,而王安忆却是一副人间情怀,对一切人心的险恶都怀着巨大的悲悯。
王安忆与张爱玲都是书写爱情的高手。在对爱情的描写中,体现着她们对于虚无和困境的不同认识和探询。
在张爱玲的《年轻的时候》中,潘汝良从陷入对俄国女郎的暗恋到彻底自拔,简直可以用迅捷形容。在他知道她的一些烦恼时,他感到“现在比较懂得沁西亚了。他并不愿意懂得她,因为懂得她之后,他的梦做不成了。”在他发现她竟然是个邋遢的女人后,“他竭力地使自己视若无睹。他单拣她身上较诗意的部分去注意,去回味。他知道他爱的不是沁西亚。他是为恋爱而恋爱。”他甚至在背地里学会了说:“沁西亚,我爱你。你愿意嫁给我么?”可他没有说出口来,并开始反思:“只有年青人是自由的。知识一开,初发现他们的自由是件稀罕的东西,便守不住它了。就因为自由是可珍贵的,它仿佛烫手似的——自由的人到处磕头礼拜求人家收下他的自由。……汝良第一次见到这一层。他立刻把向沁西亚求婚的念头来断了。”
在听她说要结婚时,汝良也“只是望着她,心里也不知道是如释重负还是单纯的惶骇。”在参加她的婚礼时,汝良的反应竟然是“不能不钦佩沁西亚,因而钦佩一切的女人。整个的结婚典礼中,只有沁西亚一个人是美丽的……她自己为自己制造了新嫁娘应有的神秘与尊严的空气,虽然神甫无精打彩,虽然香火出奇的肮脏,虽然新郎不耐烦……”
这个潘汝良实在很透彻,他眼中的爱情和婚礼简直就是一个人生的魔界,而他也真的像张爱玲笔下那个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个潘汝良几乎就是张爱玲的化身。张爱玲对人生有梦想,但又感悟到人生不过是幻象,她很轻易地在梦想和幻象之间划上等号,把现实给否定了。当然这也使她能够独步于人群之外,对笔下的人物进行居高临下的透视。
相比较而言,王安忆则富于同情。从她客观的描述中能体味到,她是怀着同情之心走近人物,聆听她们心灵的呼唤。她们身上的精神气息更为浓烈,也许她们争取精神的过程充满了种种不堪、屈辱,但她们都在为自己对于生活的想法不屈不挠地努力。《我爱比尔》中的阿三实在荒谬得可以。她以为自己喜欢比尔,其实她喜欢的不是比尔,而是他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在初次的情感失败之后,王安忆又给她许多的机会,从努力绘画到小有名气,到再度幻灭,到大堂,到劳教农场,到遭遇阳春面,到逃走,到碰到处女蛋,阿三的人生阅历在不断展开,对于人生的体悟也渐渐不同于从前,终究获得了一些见识。
她们对于虚无的认识是在不同背景下形成的。
在我看来,张爱玲并非如王安忆所言是“哗”的一下走到虚无去了[2 4]。她身后有两个战争的背景,一个是欧战,一个是港战。1939年,因为“欧战”爆发,张爱玲以伦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改到香港大学注册入学。在港大的二年多,“发奋用功了,连得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1941年“港战”又起。这对于正在求学的张爱玲来说无疑是一个噩耗,可对她的文学前途而言却是一个“福星”。她在《烬余录》中以少有的敬意描写历史教授佛朗士,“可是他死了——最无名目的死。”生命危在旦夕的感觉确实很恐怖,这也奠定了张爱玲的创作基调必然是苍凉的,虚无的:“想做什么,立刻去做,或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战时香港的所见所闻……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
的确,在战争与死亡这样苍茫的背景中,张爱玲对于物质生活的爱悦和描摹就落到了虚无之上,她是在战争的灰烬上重新活过。因而她笔下的人无不充满了生的力量,不论是邪恶的物质力量的七巧,还是理性的斗争力量的潘汝良,还是欲望的肉体力量的葛薇龙。她们泥足深陷在人性的魔界之中,很难向神界做哪怕一丝的争取和眺望。
而王安忆的人生没有这样的战争背景,而是一个插队背景。在这一时期,城乡差别让她体会十分深刻,并成为她挥之不去的梦魇。她反复书写这一段时间:1982年的《流逝》,1986年的《69届初中生》,1995年的《长
恨歌》直到1997年的《妹头》,还有大量的短篇小说。插队对别的城市孩子的冲击已很大,对生活优越的王安忆更是如此。她的虚无感很可能来自于这一时期。比如她会通过笔下的欧阳端丽感慨文革十年之后,一切又似乎回到了从前,而自己的一段生命却是真实地流逝了。但也正是这个阶段使她有幸看到并正视了世界的另一种形态——贫瘠而广阔的乡土,令她经受了意志的磨砺,精神变得强大,能够赋予笔下人物同样强大的精神力量。
在王安忆这里,因为对于神界的向往,而对笔下人物产生一种地母精神,人物是非曲折,她都一概包容,与人物同甘共苦,感同身受。张爱玲则否定了神界的存在,常常以一种小女子的任性与挑剔,将人物的是非曲折都观照一番,笔致尖酸刻薄,意境更是近乎冷酷的苍凉。再返观她们对于女性自我和女性书写的不同认识和表达,也就不难理解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给一位朋友的条幅中写道:佛界易进,魔界难入。英国诗人布莱克也曾经说过:任何一位伟大的诗人,总是站在魔鬼的一边。可我认为这种看法有其片面之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各在佛界与魔界的两端,但并不妨碍他们各自的伟大。
在谋生与谋爱、魔界与神界的不同关注中,张爱玲与王安忆走出了各自的文学道路,给我们写出了各自不同的世界,为人性书写做出了不可小视的贡献。
注释:
[1]张爱玲《私语》,《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第102页。
[2]、[3]、[4]、[6]、[7]、[8]张爱玲《谈女人》,《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64-72页。
[5]张爱玲《有女同车》,《张爱玲文集》第四卷。
[9]《第二性》,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页。
[10]、[11]、[13]、[16]、[17]王安忆《男人与女人,女人与城市》,《语言的漂泊》,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407页。
[12] 《从现实人生的体验到叙述策略的转型——关于王安忆十年小说创作的访谈录》,《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14]王安忆《漂泊的语言》,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419页。
[15]、[19]王安忆《问女何所爱——有关电影〈风月〉的创作对话》,《王安忆说》,第62、61页。
[18] 文学对话录《〈小鲍庄〉·文学虚构·都市风格》,《语文导报》1 987年第4期。
[20]王安忆《死生契阔,与子相悦》,《寻找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21]王安忆《地母精神》,《文汇报》2003年2月17日。
[22]刘颋《常态的王安忆非常态的写作——访王安忆》,《王安忆说》,第230页。
张爱玲与萧红作品比较
不同的小人物,不同的女性 - --------论萧红与张爱玲的人物形象塑造 龙瑞10022154 摘要:同一时代下的两位女性作家对不同女性的刻画,在人物选择上,一个落脚于农村妇人,一个落脚于都市女性。 关键词:女性,人物形象 十九世纪的中国,出现了大批的文学创作者,虽然男性居多,但也有不少女性作家,而且这些女性作家,更为关注女性生活。这其中,萧红和张爱玲就是典型的代表。 虽然萧红长张爱玲近十岁,但却是同样经历了中国的动乱,中国被瓜分的时期。她们生存的社会环境却极为相似:出生于较为富裕的家庭,但却从小都缺少家人的关爱,长大后又同样经历了坎坷的爱情婚姻生活,使她们对爱情都失去了信心。相似的成长经历,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两位女性作家,由于各种相似点,她们往往被放在一起。 两位作家都是及其敏感而富有才华的,作品中都自然的流露出对女性的关注。但是张爱玲的女性意识要比萧红更为强烈,并且这种强烈的女性意识贯穿与她毕生的创作。而萧红在鲁迅先生的影响之下,在其后期的创作之中,这种女性意识渐渐的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国民性”的批判精神。同时,张爱玲对女性的生存给了更多的关注与理解。所以,虽然她们都是把人物定位于普通的小人物上,但是在对人物形象描绘的深刻程度以及刻画角度都有所不同。 萧红笔下的人物,几乎不存在知识女性和自我,大多是生存在北方的广大劳动人民,将朴实、真是和麻木、落后集于一身。例如《生死场》中的麻面婆,她粗野,没有文化,是典型的北方农村妇女。从麻面婆的话语中不难看出那个时代农村妇女的粗野天性。但同时,萧红以其幽默中夹杂着的讽刺的语言功力,使人对麻面婆的形象深刻难忘。萧红把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麻木及冷漠刻画的淋漓尽致。 虽然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也是小人物,但这些女性大多都是都市女性,她们不像萧红笔下的那些女人。她们有思想,而且不乏进步的思想,她们很多时候是走在时代的前端的,她们渴望冲破某些封建或腐朽的枷锁,但是又由于一些无形之中的东西将她们的行为禁锢,使得她们无法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从而导致了这种种的悲剧。例如《半生缘》中的曼潞,为了生计,她甘愿下海做舞女,她并不是十分的鄙夷这份工作,并且对于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还乐享其中,但是当遇到现实的问题时,比如,世俗的眼光,结婚的问题出现时,又使她对舞女这份职业感到及其的厌恶。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形形色色,对比十分的鲜明,她们的人生悲剧是不同的。 张爱玲与萧红都写的是小人物,都是女性,但是两人笔下的女性在本质上却是有着不一样的。萧红笔下的女性大多是东北的农村妇女,而且其中看不到作者
简析张爱玲作品的艺术特色
简析张爱玲作品的艺术特色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她的作品,与政治无关、与民族无关,是大上海一个世纪的喧嚣华丽风流云散的寓言,是人性中最让人绝望的那一层窗户纸。她的这种写作姿态成为以后小资们竞相效仿的范本,在小资写作中你永远看不到政治、国家那些大命题。她成名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她以自己特殊的现代性体验来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的人生世态。吴福辉充分肯定了张爱玲对旧家族在大都会的际遇命运的精细表现,认为她的都市最接近上海的真面目,把中国都市文学深入到“现代都市哲理”的层面。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一文里这样写道:“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但我认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的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 很多的人给予张爱玲的作品以很高的评价,其艺术特色是值得人们借鉴的。 1、华美的语言和缤纷的意象——天才之翼 (1)、纷繁的意象和出色的描写技巧 院子正中生了一棵树,一树的枯枝高高印在淡青的天上,像瓷上的冰纹。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了出来。她的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色的雏菊。” (《金锁记》) 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承认,从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就描写城市生活、人生情感的当代小说作家,很少有人像张爱玲那样能够以其完美圆熟的技术、文字的功力、深刻的人生观、犀利的观察与丰富的想像力,即,是以炽烈迸发的才情成就于文坛。在那个垦荒与洪流的时代,许多作家的文学语言尚处在胡适之、郭沫若自五四时期创造的直抒胸臆的白话诗体,对创作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而象张爱玲这样优美畅达、厚积薄发的文字是很少见的。应当说,张爱玲是避于我们文学发展的潮流之下,向我们展示了文学的另外一些层面的。 文字表达中,对意象的扑捉,精当的描写,用比喻通感来写情状物以推进情节和烘托人物心理是张爱玲作品最突出的方面。这其中,包融了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总体把握。这在她的中短篇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现。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一段情景描写:“……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
浅谈女性主义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比较
■ 白宝善(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两个奇异的亮点。在张爱玲与王安忆上海传奇的书写与建构中,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张爱玲;王安忆;人文关怀 一、引 言 二、奴仆到女人的回归 [1]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的女性安忆则是以自觉的姿态来正视女性的。当女性摆脱了男权意识的控制,她们逐渐变得独立、成熟而坚强,在女性意识的觉醒中相继投入到社会生活中,饰演自己的角色,展现自己的风采。[2]王安忆的作品更多地关注女性的成长,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人文关怀。 三、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承传与拓新 张爱玲可以说是现代女性主义小说的第一人。张爱玲将自己对人生的观照凝定在普通人的身上,正如她在《传奇》的扉页上所写:“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4] 王安忆作为受张爱玲影响的作家中成就最大,对海派精髓领会最深的一位,在小说创作中继续拓展着自张爱玲以来建构的女性主义文学的新天地,并对“张派”一脉作最富有创造力的延伸。对上海这个多面体,王安忆有着理性的认识,在她的上海书写中,没有对时尚的炫耀与展览,她聚焦的是城市的日常生活。她紧紧依偎着多姿多彩、新鲜润泽的日常生活本身,在貌似风花雪月的故事演绎中,渗透着包括价值取向、审美风格、文化意蕴、市民情趣在内的民间写作立场。“上海这城市在有一点上和小说特别投缘,那就是世俗性。上海与诗、词、曲、赋,都无关的,相关的就是小说。”[5] 我们在王安忆的女性主义小说中实实在在地读出了历史的沧桑,看到了人性的善恶,可以说,王安忆是在一步步地向坚韧的人生态度靠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小说创作是承接了张爱玲透视世俗人生的衣钵,但她对女性主义人生的体会更带有主动性和自主性。在关注重大社会问题上,王安忆也表现了她独特的人生态度和鲜明的个人立场。作品在展现女性主义生活世俗的同时,也在向我们展现人性,不是知识分子的某一群体而是大众的人性。如果说张爱玲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关于苍凉和凄美的追忆,王安忆更多的带给人们的是关于人生的感悟和一种临危不乱、处事不惊的人生哲学宣言。 四、女性主义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价值 张爱玲与王安忆分别以其女性意识和人文关怀,从女性日常的生命流程入手,就生存状态、情感层面等描写女性的生存境遇,反映以女性为代表的市民精神状况。张爱玲的作品从历史场景中的女性入手,侧重表现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束缚,与女性意识觉醒的艰难历程,自发地审视女性依附寄生、自甘卑下的心理痛疾,揭示女性悲剧的深层内因,对女性的“原罪意识”进行展露和鞭挞,目光犀利,悲天悯人。作为新时期的女性作家,王安忆以平实的格调,注重描写女性主义生活场景中女性外在生存价值与内心体验,自觉致力于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权力的争 浅谈女性主义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比较 2009年第2期
叛逆者的不归路(读萧红传有感)
叛逆者的不归之路 ——读《萧红传》有感 我已记不起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萧红,并爱上这个叛逆的灵魂了。与张爱玲的知名度相比,萧红似乎并不被人们所熟知,但是她确实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其才华丝毫不亚于张爱玲。 萧红,原名张廼莹,笔名悄吟、玲玲、田娣等,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夏志清称萧红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这是我从百度百科上找到的关于萧红的简介,对萧红文学上成就评价很高,但是在这些耀眼光环的背后,是萧红颠沛流离的悲剧一生。在看完《萧红传》后,我对萧红有了更为详细系统的了解,也更加敬佩这位勇于与时代对抗的女性。 萧红的一生都在逃亡,逃避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逃避男权文化的钳制。但最终仍然死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叹所遇不淑,她的逃亡均以失败告终,但这悲剧的经历,成就了她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基础,而且她的一生从未屈服,一直在抗争直至死亡,使人们无论怎样感叹她的悲惨命运,都不能简单地把她归入弱女子的行列。她在她的时代,挣扎过,探索过。她坚持了自己的信仰,她为自由解放而战,既是为了民族,也是为了个人。她是一个时代的叛逆者,更是一个可歌可泣的勇士,用短暂的一生书写了一部觉醒女性的奋斗史。 和所有的女作家一样,萧红的思想和才华长期地被人们漠视,私生活却不断地被爆炒。以至于关于她的生平,至今仍然总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萧红是一个个性主义者,也是一个个性解放的先驱。她出生在辛亥革命的年头,又成长在具有维新倾向的乡绅之家。这使萧红在童年时代就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启蒙,具有向封建礼教挑战的自觉。这也为她未来的传奇一生奠定了基础。 萧红是一个十分与众不同的女性,在她被王恩甲抛在东兴旅馆逃都逃不了的时候,怀着身孕的她从未放弃生的希望,想尽方法向外界寻求帮助。就在这个时候,她遇上了她这一生永远的痛-----萧军。书中萧军和萧红的一次关于死亡的谈话让我对萧红钦佩不已。萧军问萧红:“你为什么还要在这世界上留恋着?那你现在,自杀条件这般充足。”萧红答道:“我吗?……因为这世界上,还有一点能使我死不瞑目的东西存在,仅仅这一点,它还能系恋着我。”萧红在极端绝望的情景中,仍然怀着生的执着,本能地抗拒着死的诱惑。这是那个时代的女性绝对无法做到的。这种精神一直贯穿着萧红的一生,使她在将来不管遇到多大的痛苦和绝望,都保持着一颗跳动着希望的火热的心,这是同时代女性绝对无法做到的。这也是我如此佩服萧红的最主要的原因。 真正使萧红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闪闪发光的是她惊人的才华以及她留下的超越时代的作品。她创作的《生死场》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使当时麻木的愚夫愚妇们终于在亡国灭种的危难中警醒了。在短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她写下了近一百万字的作品。她由幼稚到成熟,由投身到左翼文艺思潮到逐渐独立,有意识地疏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思想经历了明显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在这一路上,萧红走的并不容易。萧红的思想是深刻的超越时代的,以至于受到同时代人的质疑,批评和谴责。她关于生殖和死亡,人生与人性的看法以及对作家和小说的独特见解都是她思想的结晶,这是那样的深刻而丰富。但在一个救亡压倒一切的时代,注定她很难为同时代人所体会,她只能独自一人行进在布满荆棘的不归之路上。因此,萧红是孤独寂寞的,却又是伟大的。因为她的思想是深邃的,她的目光穿透了漫长的世纪,望着人们的未来。她属于那种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的作家。 其实,萧红能有现在这么大的成就和一个人的帮助分不开,这个人就是鲁迅先生。萧红和萧军在上海期间,生活穷困潦倒,是鲁迅先生一路帮助他们,并使他们在上海有了立足之地。萧红的《生死场》也是在鲁迅先生的鼓励下创作出来的,不仅如此,鲁迅先生还为《生
张爱玲前后期作品分析——以胡兰成为分界
张爱玲前后期作品分析——以胡兰成为分界 作者七声摘要张爱玲是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 的女作家, 1943 年《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发表标志着她正式步入文坛,自此而后的几十年间,她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金锁记》、《倾城之恋》、《雷峰塔》、《易经》等等,都可以被成为经典。但是,其前后期作品的特点却有着较大差异:前期作品以华丽而悲凉的风格为主,重点描述爱情与欲望的角力;后期作品却以略显杂乱的平铺直叙书写自己洞见世事的人生体悟。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差异,一方面是因为早期家庭及社会背景的影响,使张爱玲既具有遗老遗少的部分习气,同时也对爱情抱有较为悲观的态度;另一方面胡兰成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张爱玲的人生观和创作方向,在经历了对爱情的憧憬和破灭之后,她从写别人的故事转而写自己的故事,用文字记录、感悟人生。本文将从张爱玲前后期作品的概况入手,分析不同时期其作品的不同特征,同时分析前后期作品是所以会产生差异及以胡兰成为分界点的原因,以期对研究张爱玲极其作品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张爱玲;前后期作品;胡兰成;原因;影响 abstract Zhang Ail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female write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1943,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incense" marks her formal entry into the literary world. Since then, she has been working hard for a few decades. Works: "Golden Lock", "Allure Love", "Thunder Tower", "Book of Changes" and so on, can be a classic. Howev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ks before and after it has a big difference: pre-works to gorgeous and desolate style, focusing on the description of love and desire wrestling; post-works are slightly messy straightforward to write their own insight into the life of life insights. The reason why there will be such a difference, on the one hand because of the impact of early family and social background, so that Zhang Ailing not only part of the legacy of the old habits, but also have a more pessimistic attitude towards love; the other hand, the emergence of a certain degree of Hulan Cheng Changed the love of Zhang Ailing and creative direction, after experiencing the vision of love and burst, she wrote from someone else's story to write their own stories, with the text recorded, sentiment life. This paper will start from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Zhang Ailing 's works in the early and late period, analyze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his work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analyze the reasons why the works will be different and the reason of Hulan' s demarcation point, so as to provide some help to the study of Zhang Ailing 's extreme works.
李煜、李清照写“愁”之异同
李煜、李清照写“愁”之异同 诗词文本的比较阅读是一种独特的阅读思维过程,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对教学文本的分析、归纳,求同存异,最终达到鉴赏诗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目的,并同时掌握鉴赏诗词的方法和手段,真正提高诗词鉴赏的能力。笔者试从《虞美人》、《声声慢》两首词对“愁思”的抒写出发,从“愁思”的内容和表现手法两个角度对文本进行比较阅读,教会学生找到一种全新的诗词阅读鉴赏方法,“将厚书读薄,将薄书读厚”。 一、“愁思”的内容 李煜、李清照愁思的基本内容是“国仇家恨”。写《虞美人》时的李煜早已国破家亡,漫长的囚禁生活开始风干他作为君主的自尊和对亲人的思念。“春花秋月何时了”,他诅咒眼前的一切,娇艳的春花、明朗的秋月,在作者的眼中只能增加他无限的故国之思、忘国之痛;“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朱颜”泛指故国的宫女,传达出的是作者对娥皇、母亲等亲人的无限眷恋。《声声慢》虽然没有直接写亡国之恨,但全词抒写的是李清照经历坎坷人生后的伶仃孤苦,正
是由于国家的变故、民族的危亡造成了她的个人遭遇,山河破碎给她留下了抹不去的心灵伤痕。“燕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作者因国破从北方寓居江南,见到北雁南飞,便生怀对亡故丈夫赵明诚的怀旧悼亡之情。 同是抒写“亡国之恨、散家之痛”,但由于两人的身份和性别的不同,决定了两人“愁思”在文本中具体表现的内容不同。“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把愁思比作充盈奔流的江水。作为一代帝王,李煜从理性、奔放的男性视角抒发情感,是那么的浓烈、磅礴,给人以独特的厚重感,他的“国仇家很”是如滚滚的江水一般喷涌而出。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虞美人》意象的使用上,“春花秋月”、“雕栏玉砌”打下了吟风弄月、莺歌燕舞的帝王生活的烙印;明月下偌大的故国,还有那无数的后宫佳丽,虽然都是回忆,但也是李煜作为贵胄子弟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身份地位的象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里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出生在富贵之家的李清照,写“愁思”时,体现出了女性独特的细腻和灵巧。同样是把“愁思”比作连绵不断的江水,但李清照的“愁思”如秋日黄昏的细雨,点
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比较
谈张爱玲与王安忆 摘要:张爱玲作品中的女孩子大多数活在物质缺乏的世界里,她们是为生活而选择了爱。而王安忆的作品恰恰相反,她直接切入女性情感的话题,说出她们是为了爱而选择生活。从谋生出发的张果断勇敢地塑造了女性神话,从谋爱出发的王安忆则着意要塑造一种地母精神。这中间的不同与她们的成长经历有着很大关系。所以在张爱玲的眼里人生不过就是一个魔幻般的世界,除此之外的都是空有的,飘渺的。而在王安忆看来人生不仅仅是一个魔界还充满了神奇。神界是对虚无缥缈的超脱 关键词:女性神话、地母精神、魔界、神界 王安忆与张爱玲有相似的地方,她们都是以旁观者的眼光用细致深入的描述,给世人展现了一道真实而隐秘的人生风景。她们都写过都市,都对女性的命运和人性困境有不一样的热情。单从最后一点谈,对女性命运和人性困境的书写构成了彼此巨大的分野,使王安忆从张派或者海派传人的位置上彻底独立了出来,避免因《长恨歌》之一叶障其整个创作天地之目的批评视线。 一、从女性神话到地母精神:谋生与谋爱 张爱玲的妈妈出国七八年,这段时间正是她人生成长中的关键时期。张爱玲在《私语》中回忆道:“最初的家里面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更何况是一个与父亲离了婚的母亲。她觉得她与母亲简直如同年岁相隔较远的姊妹[1],十分生疏与淡漠。没有享受过母爱一方面使她对母
爱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也对母爱产生了渴望。所以她会说:“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神勃郎’一剧中的地母娘娘”。[2]这个地母形象确实分量很大,在中西文学中可以说是独步。她以博爱包容死,创造生,想要消除一切生灵的苦痛;她明明知道生命的诞生就意味着死亡,可还是带着“痛切的忧伤”的情感去迎接一次次恋爱怀胎和生产的痛苦,然后去安抚一个个死去的生灵。为了表达对她无限的敬意,张爱玲不惜一切代价的去拥护:只有地母娘娘,“这才是女神”[3]。在她面前,除了地母娘娘所有的神灵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比如:“‘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4] 但她对女性的认识又有一些矛盾。在创作中反应的尤为显著。她对地母精神持怀疑态度,因为她从没有真正的相信过,只是作为一种假设。所以在《霸王别姬》中,她反写了传奇,变成了姬别霸王,虞姬作为一个自我反省者出现,“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十来年里,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像影子一般地跟随他”,她这样活着简直是“反射着他的光和力的月亮”,而到“她要老了,于是他厌倦了她”时,她不得不成为“一个被蚀的月亮,阴暗、忧愁、郁结、发狂”。这几乎就是张爱玲对中国传统女性命运的一种寓言化。在《有女同车》中,张爱玲发现女人谈话的主题无非是自己的上司、丈夫或儿子,这使她感到了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5]
季红真在给北大学生所作的一次讲座中曾对萧红与张爱玲作过比较
季红真在给北大学生所作的一次讲座中曾对萧红与张爱玲作过比较。她说,萧红和张爱玲都是接受了新文化教育的女性,都积极与父权制度、父权文化作斗争,这是她们传奇式人生道路的开始。而且,她们两人一生都经历着逃亡,辗转各地,艰辛漂泊。这始终贯穿着她们终生。但逃亡之路都以失败而告终。 萧红和张爱玲都始终坚持着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没有党派或官职,基本上都靠写作维持生活。但这并不表示她们超脱世外,她们都以个人化的方式关注着时代宏大的主题:文明的荒凉。萧红后期的作品中充满着孤独寂寞之感,正因为她是思想的先行者,不为他人所理解。就像萧红曾说的那样,“作家不是属于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所以她们的思考是对人生的质问,是超越她们自己时代的。张爱玲的作品适应“五四”以后的平民文学,又对“左翼”文学保持很宽的心理距离。她的作品主要表现对中国传统文化悲剧性的感悟,表现中国文化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下的尴尬,并表达了对现代文明的荒凉与毁灭的焦虑。 此外,她认为,萧张二人的写作都确立了女性的主体,并与鲁迅所倡导的“五四”新文学传统相吻合,而且她们的写作为二十世纪汉语写作提供了成功范例。 《光明日报》有关于二位女性作家的比较: 萧红,其实我并没有完全读完《生死场》《呼兰河传》,但萧红的照片给我一种清晰的感觉:烈性女子。她的文字凄厉,大约与境遇相关,她碰到的男人都不好,第一个是浮纨子弟,第二个萧军是大男子主义者,而且最后又找别的同志组合去了,端木蕻良有过于软弱的地方,萧红多少是被牺牲被辜负的。 萧红的人生跌宕起伏的,与萧军三次离合,最终离开,离开萧军意味着离开革命阵营,萧红的女子自语转变的很奇怪:一面是文化主流中的“大我”话语,一种是主流边缘”女性的“小我”话语。而大我的激烈亢进始终掩饰不了小我的忧伤失望。她也许潜意识里有自己的话要说,不为外物所蔽。当她辗转至香港,患白喉而逝,死时没有发出任何声息,虽然她曾写下了振聋发聩的文字,但文字又怎么样?总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会过去的,就象她的生命——开到荼蘼花事了。 我常想起萧红,是因为我更喜欢《小城三月》里流露着纯洁、感伤同时体验着青春快乐的萧红,还有那个跑到鲁迅先生家试着不同的衣服笑吟吟问“可好看”的萧红。想起她那单纯爽朗的笑声终于淹没于世的沉寂,那种鲜明的热闹喧嚣自此休止的空落。 至于张爱玲,到底是聪明绝决的,她将人性的软弱低微看的再清楚不过,写来刻骨入微 季红真在给北大学生所作的一次讲座中曾对萧红与张爱玲作过比较。她说,萧红和张爱玲都是接受了新文化教育的女性,都积极与父权制度、父权文化作斗争,这是她们传奇式人生道路的开始。而且,她们两人一生都经历着逃亡,辗转各地,艰辛漂泊。这始终贯穿着她们终生。但逃亡之路都以失败而告终。 萧红和张爱玲都始终坚持着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没有党派或官职,基本上都靠写作维持生活。但这并不表示她们超脱世外,她们都以个人化的方式关注着时代宏大的主题:文明的荒凉。萧红后期的作品中充满着孤独寂寞之感,正因为她是思想的先行者,不为他人所
萧红
应当怎样理解《黄金时代》?这是一个女人三十一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她一生的颠沛流离浓缩在一部电影里,若你喜欢就拿去吧,去看看那些她留下来的文字,那些在苦难里开出的花;若是不爱,也没有必要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权当路人走过,毕竟就算她的身世经历再怎么复杂,也不过只是一个心性单纯可怜又可爱的女人,萧红。 萧红第一个爱上的人是她的的表哥陆哲舜,但是他已经结婚了。家里的父亲给定了门亲事,她却与表哥私奔然后又被抛弃。“我的私奔事件成为呼兰县耸人听闻的恶行,我们家声名狼藉”,于是萧红独自一人流浪在冬季的哈尔滨,自此众叛亲离,居无定所。那些所谓的亲人此刻全是正义的化身都报以理所当然的白眼。 流浪的时候,她没有钱,天气又实在冷,便去投奔那个曾经的的未婚夫汪恩甲,在道外的东兴顺旅馆还同他生活了七个月。想不出这样一个连父亲都不愿投靠的女孩子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去和那个男人在一起。在一个和平时并无什么两样的夏夜,汪先生独自离开了欠了六百元钱的旅馆,从此了无踪影。为什么呢?或许是
为了报复吧,报复这个女人曾经的逃离使他和他的家庭所受到的耻辱。真实答案无人可知。旅馆老板说倘若萧红拿不出钱,便要等她生了孩子拿她做妓女赚钱。是了,她还怀了孩子,可是那个男人跑了,或许他的离开是必然的,命运的齿轮总是环环相扣。 在旅馆那间昏暗的仓库里,三郎第一次见到了萧红,那是命中的相遇,“她有一张近于圆形的苍白色的脸幅,镶嵌在头发的中间,有一双特大的闪亮的眼睛”,“什么是爱,爱便爱,不爱便丢开,要是丢不开,便任他丢不开”。这样的两个人,是注定的在一起,却又是同样的尖锐。后来,萧红生下了一个男孩,没几天,便送了人。他们俩都没什么钱,用盐巴沾了面包吃,连旅馆的被子都租不起抱成一团取暖。 之后萧军找到了份家庭教师的工作,日子总算好过了些。萧红穿着萧军的夹袍俩人一起走着,“电灯照耀着满城的人家,钞票带在我的衣袋里,就这样,两个人理直气壮地走在街上”,要是日子过得一直如此简单。后来,他们与鲁迅相识,彼此之间无话不谈,就连之后二萧情感生变后,萧红也常常去先生家里。后来,萧红一个人去了日本。再后来,他们俩在关于战争去留的问题上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分歧,萧红与萧军永远地分开了,我愿意相信这是两人此生都最为刻骨的感情。 萧红二十七岁和端木蕻良结婚,谈不上真爱,也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萧红眼中的端木是胆小的懦弱的,或许仅仅是因为情感空窗期的陪伴;是骆宾基送走了萧红,据说他是萧红弟弟的好友,慕名而来。1942年,萧红病逝于香港红十字会设于圣提士反范女校的临时医院,享年三十一岁。 萧红的一生是孤苦而无依的,但这并不妨碍她的作品对于生活的穿透力。我们无法知道究竟是苦难造就了她的作品,还是苦难的生活使她不能够全心全意地创作。每一段感情似乎她都是当做一生的爱去付出,可是那些男人,如萧军如端木蕻良都是和他们各自的妻子白头偕老子孙满堂,只有萧红一人早早地就去了,没能留下一儿半女。祈求了一辈子的安定,却从没有过片刻的平静。 《黄金时代》是一部优秀的影片,现如今这种文艺片并不是很卖座,但还是依然尽心尽力地还原了一个朋友们眼中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不空洞的萧红。不可避免的是这样一个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是以情感为主线,难免造成私生活混乱的表象,有人会说同样是民国时期的女神,张爱玲就很专一,也没有碾转于一个又一
张爱玲作品特点
张爱玲是一个别致的女子,她用作品写就了一生的传奇,她的故事里那些鲜活生动的人物,让人欲罢不能,无意间的走近而成为永恒的张迷,她的文字雅俗相触,中西合璧,传统意让与现代的技巧相统一,时隔50 年她的作品依旧新鲜,她笔下的人物依然是前精神的,虽然她已远离人世,而她的文字依然在滚滚红尘中徜徉。 1、作品中浓郁的市井气息张爱玲的小说中没有大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有的是小人物的种种俗欲,为了安身立命,而不得为之的命运。贫穷的白流苏,葛薇龙;都不得为之的生计而以婚姻,青春为代价,换取物质的满足。出卖一生,终于成为富有者的梁太太,曹匕巧,在扭曲的灵魂中挣扎。葛薇龙对衣饰的喜爱,白流苏为长期饭票——婚姻的算计。梁太太那唯一的乐趣,曹匕巧死守着用青春换来的金钱。在她笔下那么生动,那么无耐,让我们在摇头叹息之后重又省视自己,自己身上有多少她们的影子,俗拉近了与人物的距离。她们就在我们身边,张爱玲说:“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 2、浓郁的旧小说色彩张爱玲的小说几乎都采取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以“说书人”的身份来讲故事。如《沉香》,第一炉香一开篇就是说书人的口:“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率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听我说一段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中国旧小说多是单条线索,按时空的先后演变顺序来结构故事。脉络清晰,井然有序。张爱玲的小说多市如此,无论穿插多少倒叙,插叙补叙总体线索不变。例如《倾城之恋》,《封锁》等《金锁记》《十八春》尽管开头使用了倒叙,但文章展开,很自然转为以时空变化为序,以人物性格命运为线的结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依次铺开。她的小说有无巧不成书,曲折性,传奇性,一波不平,一波又起等传统的旧小说方式。俗增加了耐谈性。俗雅——华美后的苍凉。张爱玲的作品在这俗人俗欲里,又有一丝深层的味道。人物对命运的抗挣与无耐。世态炎凉,让爱思索的读者诅嚼,如《倾城之恋》白流苏,是一个28 的离婚女子,她出身在一个没落腐朽的旧式家里,排行老六,20出头,坚决同丈夫离婚,回了娘家,她的钱渐渐被兄嫂花光,又开始冷落嘲讽,劝她改嫁。母亲也袒护兄嫂,为了生计,她向往着与范柳厚的婚姻。一个有钱。放荡,在英伦长大的公子哥。各家太太们都争抢把女儿嫁给他。而他只想流苏当他的情夫在一场场较量中,白流苏被逼到没有退路的绝境——做了的情妇。而此时香港战争爆发,在这乱世中,两人相互依存,于是结成夫妻。白流苏似乎是赢了,战争而在这场婚姻后面,难掩她心中的荒凉。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写这篇小说,是为了表现“苍凉的人生的情义” 张爱玲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白流苏与范柳原有多少爱情,婚姻又过的怎样,我们只有想象。有相同境遇的人,大抵也希望有白流苏式的传奇,而背后的苍凉与无耐又有谁知了,这就是张爱玲,就是在圆满后,也不忘告诉你“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子。” 3、多种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雅与俗的完美结合。 张爱玲不仅从《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吸取营养,她还在西方现代文学中吸取了心理分析,意识流,通感、蒙太奇等技巧方法,在小说中灵活应用。 1、心理分析对揭示人物的潜意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傅雷对于张爱玲小说尤其是《金锁记》中的心理分析给了高度评价:“作者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兄长的独白或枯索繁琐的解,她利用暗导,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曹匕巧是一个乡下开麻油店小户人家的女儿,父母早亡,爱钱的兄嫂把她卖给了姜家,她的丈夫是一个害骨痨的残废人,她本泼辣风情,有对爱情的向往,但在这个大家庭里。她只能守着残废的丈夫,而她的出身,作派又受人鄙视。当她看到小叔子季泽,她以为她爱上了他,而季泽打定主意不碰加里人,而她示爱被拒绝,张爱玲写到“她睁者眼只沟沟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的蝴蝶标本,鲜艳而凄伧”她的心理感受就通过这蝴蝶标本生动的展现在读者眼前了。死去了,只剩下美丽的躯壳。因为美丽,更显苍凉。而她的世界里欲发只有金钱。张爱玲用了“蒙太奇”的手法,概括了七巧的十年,象一只美丽的蝴蝶标本呆做镜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等待来的爱情,只有日渐苍老的容颜。区区百字,读者感受了时光的流逝,感受了七巧的寂寞。“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遥遥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镜子。镜子里发映着的翠竹窗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眼看
李清照、李煜、纳兰性德对比
问世间,愁为何物,竟如绵绵江水,从古流到今,从春流到秋,赚得英雄长扼腕,赚得女儿泪湿帕,赚得世人竟白头。且不言渭水河畔、苍苍蒹葭中追寻伊人的秦国少年爱情梦的苦涩,也不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李谪仙“白发三千丈,愁缘似个长”的悲愤,我们只读一读亡国之君李煜、文士之女李清照、宰相之子纳兰性德三位词人遗响后世的那些天籁之作,就足以愁煞人了。 南唐后主李煜(937-978), 24岁即位,史称南唐后主。即位时南唐已摇摇欲坠,赵匡胤新建立的大宋对南唐政权虎视眈眈眈,李煜只顾享乐,对宋称臣纳贡,以求偏安一方。作为一国之君,他在政治上无所为,但却是一位艺术天才。“聪颖敏慧嗜书成性,善诗文,兼通书画,更妙于音律”。① 启功也说:“一江春水向东流,命世才人踞上游。末路降王非不不幸,两篇绝调即千秋。” 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其实,李煜天性本是一位诗人,他生性率直,敏锐善感,风流多情,偏偏被命运推上了乱世君王的宝座,这是南唐的不幸,但却是诗人的大幸,正因为此,南唐很快地亡国了,但文学史上却出现了一位绝少得天才。使亡国之君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清沈雄《古今词话》语),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这些后期词作,凄凉悲壮,意境深远,已为苏辛所谓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至于其语句的清丽,音韵的和谐,更是空前绝后的了。 李煜前期的词或描写他酣歌醉舞、豪华享乐的宫廷生活,或描写他跟后妃或歌女的艳情生活,或描写缠绵的相思情意,缺乏社会内容和思想意义,带有明显的庸俗气息,格调不高,但后一类比之前二类,较少欢乐的情调和轻佻的意味,而写得惆怅曲婉、哀怨动人。如《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清平乐·别来春半》等。在饱尝了人生苦难后,他的词更不同于一般士大夫的失意愁闷之作,如《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宵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这是李煜被俘之后的反思之作,不仅展示了亡国之时的悲苦情怀,而且追悔了自己当年的安逸生活,饱含着一种沉痛的悔恨之情。又如《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首词,字字血泪,是发诸胸臆的亡国之音。末二句自问自答,以东流的一江春水来比喻愁情,写出了绵绵无尽又浩渺无边的情思,意境既阔大又深远,引起后世无数读者的共鸣和赞美。清人陈廷焯评云:“一声恸歌,如闻哀猿,呜咽缠绵,满纸血泪。”(《云韶集》卷一)无疑道出了许多人的共同感受。 李煜后期的词基本反映的是这种情绪,所以李煜词的主题乃离家丧国之恨。 继李煜之后,善写缠绵悱恻之愁情的大词家有北宋浅吟“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柳永,和低唱“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秦观,而此二位寄情秦楼楚馆,终未识得人间苦难,毫无历史的质实和沧桑感。一变宋词“过于纤弱,气格不足”之风的是光照千古的女词人李清照。
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中的都市女性比较
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中的都市女性比较 摘要:张爱玲和王安忆这两位身处不同时代的女性作家,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都市女性,始终将女性作为立文的视角。在她们的小说中,这些女性都有着殊途同归的命运——回归家庭。但是在回归的心境上却有着天壤之别。关键词:生存状态女性命运张爱玲王安忆【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728-2462(2009)01-0016-01 西蒙·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女性不是从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应该担当怎么样的角色,应该走向哪一条人生路,而是在不断的寻求中才找到自己。张爱玲和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们就在这样的寻觅中不约而同的把回到婚姻,回到家庭作为自己人生的归宿点。只是在回归的心境上有着天壤之别20世纪40年代,经历了五四女性的崛起,娜拉出走,尽管“女性觉醒”、“个性解放”等口号振聋发聩,但事实上,妇女在社会、经济、婚姻等方面的角色并未改变。生活在旧文化没落背景下的妇女,其命运更是处在人生的最边缘上,她们最好的出路是找到一个好的归宿,成为一个守旧的妻子。学历、工作不过是“一份昂贵的嫁妆”。都市女性只能是回归或堕落,没有生存能力的流苏们只能选择为婚姻而奋斗的方式以求得安稳的人生。流苏由于不愿意回到夫家去守寡,更不甘心就此堕落,于是张爱玲只得让她攀附一个有经济保障的男子了。张爱玲笔下许多和流苏一样的女性,她们缺少自主意识,不仅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而且在人格上,感情上都不能摆脱对男性的依附。流苏自己就说:“我又没念过两句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么事?”于是她决定用自己的前途下赌注,来赌一场并没把握的婚姻战。要不是香港之战成全了她,她也只能落入“情妇”的道路。而女学生葛薇龙的出走是彻底的“堕落”,进了梁太太和乔琪乔设计好的婚姻圈套,从此不是替梁太太弄人就是替乔琪乔赚钱。“无论新派还是旧派,这些女性都是自觉自愿地甘居于男性的脚下,心履斑斑,情感错混,在千疮百孔的感情世界里挣扎。”有的也曾有过自己的幻想,自信与希望,只是在那样的社会时代里不再知道何处是岸,何处是天堂。只是在滚滚红尘里挣扎着挥动了几下胳膊,明明知道挣扎无益,也不再挣扎了。执著也是枉然,便舍弃了。最后以至于幻想贬值,自信破灭,人格丧失。于是“回家”或“堕落”成了她们的归路。20世纪90年代,社会谋生道路的提供,使得女性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和自主意识,她们不必再依附于男性来换取物质财富。她们明白自己的幸福就在自己的一双手上。正如王安忆所描绘的上海女性:“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她们坚决,果断,严思密行,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她们明白,希望就在自己的一双手上。”譬如《逐鹿中街》中的陈传青把所有的目标都放在她所创造的这个家庭上,每天精心调制饭菜,把丈夫收拾的干干净净,自己织着暖融融的毛线,她觉得满足了。《桃之夭夭》里郁晓秋面对何明伟的背叛没有表现出太大的伤痛,但是当抱着姐姐留下的孩子和看着姐夫失去爱妻的伤痛时,她却绽放出了一个女人博大的情感。从此,心甘情愿地担负起照顾姐夫和他孩子的责任。可见,回归家庭,做一个好女人是王安忆笔下都市女性的追求。洗尽铅华,走入婚姻,不管曾经以怎样的心态回归的都市女性们,从此就真的过起平实安稳的生活,找到幸福的所在了吗?现实生活中女性在家庭中所遇到的尴尬让她们开始怀疑。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所以,对未来充满不安全感,对现实又显出惊心的精明。纵然是有着惠质兰心,但是现实又迫使她们不得不委曲求全以在婚姻中求得安稳。所以,无论是拼命逃离娘家的流苏,还是对姑妈家感到厌倦的葛薇龙,她们最终还是步入了以婚姻作保的家庭。但是,流苏们一边回到婚姻中做一个靠丈夫的光的反射才可生存下去的月亮,一边又在对自己这样的命运安排进行反思。《霸王别姬》中虞姬就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个月亮,楚霸王以他太阳的光反射着她的存在,“她怀疑她自己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活着,为了他的壮志活着。他知道怎么运用他的佩刀,他的长矛,和他的江东子弟去获得他的皇冠,然而她呢?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渐渐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以
张爱玲小说赏析
摘要:张爱玲小说从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女人角度给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社会、认识男人、认识女人的新天地。本文将从人性弱点、女性视角、悲凉的语言等主要三个方面来对其小说进行解读。 关键字:张爱玲、人性弱点、女性视角 从心里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孩童时期的经历会对其以后成长和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对于一位作家而言,这种现象更为普遍。而张爱玲显然也不能脱其窠臼。“本名张煐。1920年9月30日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麦根路313号的一幢建于清末的仿西式豪宅中。祖母李菊耦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不过她的童年是黑暗的,生母流浪欧洲,剩下她和弟弟在父亲和后娘的监管中成长”(A)。童年时的生活经历,对其作品的风格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阴影。下面我就从人性弱点、女性视角、悲凉的语言这三方面来解构张爱玲的小说。 一、人性的弱点。坦白的讲,张爱玲的小说人物多给人以暗淡 的颜色,几乎在里面看不到主流世界所赞扬的积极与进取的人数态度。主人公的身上,或者说是作者张爱玲本身就想给我们展现的是人性中那些丑陋与不堪,把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简单地总结一下,她的笔下主要有这三种人。 (1)由性压抑而变态的人 海蒂性学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论述“最令人愤怒之处,便是让每个原
本性欲正常的女人,反而觉得自己不正常。女人除了正常的性欲遭到剥夺之外,还被教育成要深自内疚,其实她们根本就无须自责。驱使她们为了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病症去寻找万灵丹,只会将她们推向永无止境的自疚与不安中”。(B)海蒂明显是收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的影响。巧的是张爱玲也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她从性压抑这个点出发,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由于压抑而变态的人物。在《金锁记》中就描绘了这样一个人,她为了金钱嫁给了一个患有痨病的性无能者,却又因为情欲不能得到满足,转而去破坏儿子的幸福婚姻。这个人叫做曹七巧。对于曹七巧这个人物,有很多人进行分析解读,其中关于性压抑不被满足这一观点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 (2)自私的人 不难看出,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女人,都给人一种典型小女人的形象。自私而自怜,其中自私是主要的。就连张爱玲自己也说过一切小说中都离不开自私的坏人。我想可以这样去理解,她只是想从自私这样一个任性的弱点去窥视人性更为深刻的一面。或许女人的美貌可以成为社交的妙药,这一点很多人也包括很多作家都去描写过。张爱玲写的《琉璃瓦》中有一个姚先生,他为了自己的事业自私的利用女儿的美貌,不管她幸福与否。貌似很多作家都认为人最自私莫过于利用自己的女儿,矛盾的《子夜》里也有类似的桥段。 (3)对命运逆来顺受的人
张爱玲文章分析
引言 在二十世纪文学殿堂中,张爱玲是一位很特别的女作家。她在四十年代脱颖而出,大红大紫,五六十年代在港台,八十年代之后在大陆掀起了一股经久不息的“张爱玲热”。此中缘由,近年来许多作家多有阐述。但仔细想来,张爱玲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她的小说以一种纯粹的“个人式”的参与,综合了都市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总体特征,她的小说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五四传统新文学,也不是一般意义的通俗文学。她一方面提升了现代都市通俗小说的品位,但同时她又是都市文化的消费者。张爱玲在作品传播过程中有意识的把自己的作品纳入商品运行的轨道:传者受众媒介等几大要素都受到了张爱玲的有意识并有效的关照。她既着力寻找商品本身即文学作品的卖点,努力体察受众的接受心理、阅读偏好,又十分注意媒介的准确选择与有机组合,这种自我炒作式的商品行为是张氏小说能够畅销的重要因素。 本文试图从张爱玲小说畅销因素这一视角切入,把张爱玲的作品作为一种商品,置于四十年代特殊的文化市场背景中,以市场传播学的角度加以考察,以期更深入的从创作心理和价值取向上把握张爱玲独一无二的个体特征。 一.寻找卖点 文学作品一经发表,便进入信息传播阶段,也是传播过程的主要阶段。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张爱玲十分重视受众的接受心理及接受程度。她对受众心理的掌握是比较有把握的,因此能够从各角度入手突出卖点,使读者对自己的作品产生好感和依赖感。 1、请君入瓮 首先她采用“拉”式切入法,放弃以往作家惯用的自说自话硬性倾销的传者中心的传播姿态,把自己的故事或感受当作不相干的外物突兀地、一股脑地塞给读者,而是充分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欣赏口味,以一种细致的、商量的,拉家常似的口吻淡入,利用文字的移情效应,不知不觉中吸引读者的关注和感情投入。“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
